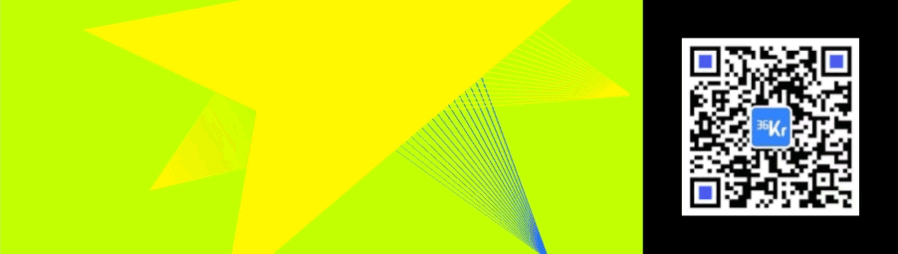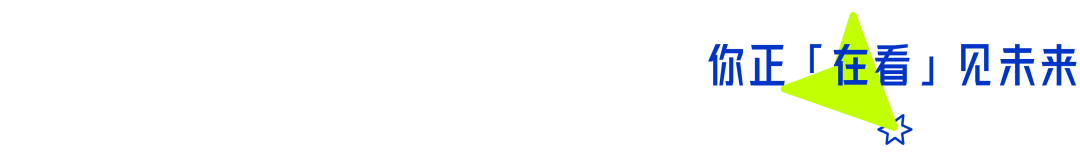中关村这个团队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外卖骑手队伍之一,成立于2015年,如今已从十几人的小团队发展壮大到了八百余人的大团体。...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,保利特别不好意思,他觉得周围都是北大学生,他自己是个送外卖的,还穿着制服,怎么好意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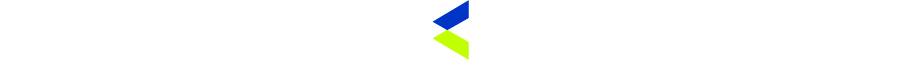
几年前,一条“北大博士后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”的新闻,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、博雅博士后陈龙跻身公共讨论视野。作为每天穿梭在城市里的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,外卖骑手构成了这个平台经济时代里最典型的零工样本。早在2018年,陈龙就开始了对外卖骑手群体的研究和体验。为了完成博士论文,他加入了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骑手站点,扎扎实实地跑了半年外卖。2024年底,他将自己亲身体验和研究的结果和16万字的采访资料,汇集在了新书《数字疾驰》里。
陈龙在前期调查时发现,仅单一平台的公布数据,就有约300万外卖员,“但这300多万人不是在一个实体的公司,而是分布在全国2000多座大大小小的城市里,每天走街串巷,看起来杂乱无章,但都能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你手里。”陈龙好奇,这背后的主导秩序究竟是什么?本应赋予人更大灵活度的数据,如何编织成困住人的庞大网络?随着科技的进步,资本对劳动控制的强化、系统及其背后的“数字控制”,又如何构成了今天这种独特的劳动秩序?《数字疾驰》共分为三篇,从骑手团队的人员构成,到亲身上路跑单的亲身感受,从“人造单王”女骑手,到“挂单”“报备”等具体而微的平台漏洞,全书以“网”“线”和“点”的结构,将骑手与平台系统、商家、顾客、站点、保安甚至交警之间的复杂互动模式串联起来。《数字疾驰》以局内人视角,揭示数字控制之下新型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如今,书中详细呈现的几位受访者,大多都已经不再送外卖了。有的去南方进了工厂,有的做起了保险销售,有的回老家带孩子。结束研究后,陈龙又花了三年多时间进行样本搜集与采访。最终,他得出结论:随着科技进步与资本对劳动控制的强化,平台、系统及其背后的“数字控制”,构成了新的劳动秩序。也正是在切身体验过这一职业后,陈龙意识到,某种角度而言,系统的确可以困住骑手,但永远无法真正困住人,也无法参与真正属于人的灵活性与复杂性。以下是陈龙的讲述。
成为他们
2018年夏天,我还在念博三,住在北大的一座学生宿舍。每天下楼都会路过很多外卖骑手在门口等着学生下来取餐,但我天天见到他们,其实都有点熟视无睹。后来,是在我导师的建议下,我最终决定将这一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确定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。
确定下来后,我意识到自己首先得成为外卖骑手。而且成为一天两天、一两个月不够,我必须熟悉这个群体的工作模式。我到网上去投简历,用地址为山西老家的过期身份证,编了一堆假的经历,几经辗转,最终成功加入了位于中关村食宝街的一个站点兄弟连。站点的性质有点像平台的加盟商。外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,平台是直接雇佣骑手,但随着骑手数量越来越多,平台就不想雇佣了。因为雇佣的成本很高,要签劳动合同。于是,他们把骑手的招募和管理外包给劳务公司,加盟商们会把某一片区域的平台订单都承包下来,设几个站点,按站点招募骑手。中关村这个团队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外卖骑手队伍之一,成立于2015年,如今已从十几人的小团队发展壮大到了八百余人的大团体。我刚加入的时候,当时的站长说过一句话:“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。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,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。”不过,送外卖第一天,我只送了9单。那时候比现在贵,一单能赚8块,一天下来,我赚了72块钱。刚开始我跑得比较节制,下午三点收工后就去找骑手做访谈,跑得也不太专心,满脑子想着我的调查。我仍然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的。但随着研究进展阻滞不前,我越来越焦虑。这种焦虑大概持续一个月后,我意识到,不行,必须先放下研究这件事儿,全心全意地投入跑外卖。我所在的中关村兄弟连,毫不夸张地说,简直是“藏龙卧虎”。什么样的人都有,有创业失败的、身负债务的中年人,也有去年那部电影《逆行人生》里徐峥饰演的曾经的中产。
对他们来说,送外卖是一项可以立刻来钱的工作,不需要高学历、技术门槛,一辆电瓶车,一台手机就行。在北京,如果非常努力地跑,一个月还是能拿到1-1.5万,这对很多三四十岁忽然失去工作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。这几年一直有传言,说外卖员的平均学历越来越高。最开始是某平台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,经统计,外卖骑手群体里本科以上学历者高达20万人,研究生学历甚至达到7万,高学历外卖骑手占比20%多。但其实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。因为它面向的是平台注册的所有骑手,可不意味着所有骑手都会填问卷。比如有好几百万骑手,最后好像只收回来了6万份问卷。我接触的骑手们,大部分还是来自小地方的、低学历的。他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来务工人员,来送外卖往往是因为身上背负着经济压力。据我观察,经济压力最大的骑手大致分为三类:第一个是有养家重任的青壮年男骑手,他们是最能“拼命”的一群人;其次是单亲妈妈;最后是已婚已育的女骑手——可能老公在其他地方打工,家里还有一两个孩子。我从2018年3月开始跑外卖,直到8月底,经历了北京的早春到盛夏。天气对跑外卖的影响很大。某种程度来说,外卖骑手和他们的父辈一样,尽管远离了黄土地,但本质也是“靠天吃饭”的行业。但不一样的是,对骑手来说,反而是越恶劣的天气,越有钱赚。夏天顶着烈日走街串巷,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有多热,而是我经常穿的那件绿色T恤,一个夏天过去,竟然全部被汗水浸褪成白色了。当时我有个站点里认识的朋友,他租住在城中村自建房里。有一天,他给电瓶车充电的时候,电瓶车忽然着火了。他第一时间担心的是把人家房子给烧了,情急之下竟然直接徒手抓着电瓶就往外搬,火就一直顺着他的胳膊往上烧。前几天我和那位朋友还一起吃饭,七年过去,我还是看见他的整只手臂几乎都是乳白色的疤痕。北京的冬天比夏天更难熬。我刚开始跑的时候还有倒春寒,有时会下雪。但捂得太严实也不行,因为跑着跑着会出汗,然后就变成了外面冷风嗖嗖地吹,衣服里面却已经被汗水湿透了,我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把汗烘干。雨衣根本不管用。雨水钻进衣服里,同样只能靠体温硬生生把水分蒸干。我至少还可以回宿舍洗热水澡,但很多骑手为了省钱,都会住在没有卫生间的城中村房子里。我在书里提到的来自甘肃的保利、春生,来北京后两个月没洗过澡。我带他们去北大的学生澡堂洗过一次澡。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,保利特别不好意思,他觉得周围都是北大学生,他自己是个送外卖的,还穿着制服,怎么好意思?我告诉他,在澡堂里,大家都没穿衣服,脱光后就会发现,我们都一样。
另一种控制
大概跑到第三个月,我想要研究的问题终于开始渐渐明朗:我所在的那个平台号称全国有三百万外卖骑手,这三百多万骑手同时分布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,但我好奇,到底是谁在指挥这三百万外卖骑手?如此大体量的劳动者,他们看似有条不紊的这种生态和规则,究竟是如何形成的?与工业化生产时代相比,互联网平台劳动者似乎拥有很大的“自由”和“自主性”。所以今天我们常听到说,很多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,但不愿去工厂。在一定程度上,送外卖的确是更“自由”的。但这份自由是相对的,很多骑手口中的自由,指的是他可以在工作中“手脑并用”。他既需要不停奔波,也需要不停地动脑,一边看路线,一边和商家、顾客甚至是交警互动。相比起封闭的流水线工厂,外卖骑手其实算是一份具有社会性的工作,至少不用将自己变成劳动的机器。
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。而在赚钱差不多的情况下,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更倾向于选择更有自由的工作。但这种相对的自由之上,还是悬挂着更精细的数据控制。从取餐那一刻开始,骑手就要开始一路的“打怪”送餐之旅。路途中不可预料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红绿灯、交警、交通意外。在繁忙的中关村商圈,红绿灯对骑手来说只是摆设,几乎没有骑手会真的停下来等红灯。团队里的一个骑手顾少聪直接告诉我:你不闯红灯,就挡了后面要闯红灯的骑手的路。骑手的工作时间大多是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,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高峰期,订单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。在这期间,由于订单量激增,平台系统会进入疯狂派单状态,骑手接收起订单来也会应接不暇。一般来说,一位骑手完成一起订单的时间在25~50分钟之间,但由于高峰期系统不停地派单,每位骑手手里都积压了大量订单。而在订单时间重叠效应的影响下,每单的送餐时间会被成倍压缩。于是,一个矛盾困境诞生了:送餐时间越短,超时的概率反而越大。最理想的效率,是通过复杂的数据计算,让自己恰好置于一个两方都平衡的时间点。
在众多的“线”中,外卖骑手与平台系统之间的互动是占据主导地位的。整个劳动秩序维系的关键就在骑手服从平台系统的指挥,而平台系统不断地收集骑手、商家与顾客的数据,并将数据分析的结果用于优化骑手匹配、线路规划、时间预计、配送定价等维系劳动秩序的方方面面。在骑手工作的时候,平台会不断收集他们的所有数据,并且通过对这个数据的分析反过来优化对骑手的管理。比如,一个骑手可能在送外卖的时候发现哪个地方有一条近路,可以帮他节约时间,这个时候系统就会优化,发现你明明可以20分钟送到那里,于是就不再会给你45分钟的时间。一般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,骑手在外面奔波、抢时间,很苦很累,但我在亲身体会后发现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。刚开始可能的确觉得辛苦,但跑了一段时间以后,其实你根本不在意有多累,你在意的是系统如何给我派更多订单,让我在更短时间内赚更多钱。你就是会不由自主地想,我昨天跑8个小时,明天一定要跑10个小时,后天要跑12个小时。我昨天只跑了20单,明天就要想办法跑30单。就像我在书中提出来的,骑手是一个不断探索人的劳动极限的工作。你做这份工作的时间越长,系统其实越会扩展你的极限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,就有美国科学家提出了“数值控制(numerical control)”的概念,那时候主要是讲计算机,通过数值来操控机器或是操控人。而我们今天说的“数字控制”特指平台经济时代数字对人的控制。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,平台经济的核心是系统,而系统的核心,是数据。总的来说,平台系统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管理效率的极大提升,将劳动秩序纳入可计算的程度,实现了对劳动的高度控制和精准预测。这种控制看起来很可怕,像是现代的另一种对劳动的异化。可我想,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空间和缝隙,可以容纳人的独特可能性。
数字的盲区
2021年,一条“博士生送外卖”的新闻将我送上了热搜,接受过一次采访后,铺天盖地的媒体打电话来找我。那时候,其实我很惶恐。因为新闻报道会突出我,“博士生送外卖”的这种对比会变成噱头。直到现在,一些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还是会说,陈龙是当年那个去送外卖的博士生,这很了不起。虽然是在赞誉我,但本质上就是将我作为关注主体。而我研究的和希望呈现的外卖员却隐身了。就在昨天(采访前一天),我还和当年认识的几个外卖员朋友吃了顿饭。一共六个人,只有一个是我在2018年就认识,而且至今还在送外卖的。剩下的大多都已离开外卖行业,有两个人在卖保险,书中的其中一个主人公保利如今在浙江一个工厂里。而大家离开的原因,无外乎“太苦、太累、风险太大”。
在我体验的那半年里,刚开始我也很犹豫,到底要不要把我做研究的本意告诉大家?一方面,我担心研究者的身份会让他们产生距离感。但另一方面,我也希望自己能坦诚与他们相处,不必担心问东问西而显得可疑。直到研究快结束的时候,我才开始告诉一部分亲近的骑手,再有人来问我之前在做什么的时候,我就直说自己是个学生,放暑假想出来挣点零花钱。这么说了以后,他们反而对我产生了更多好奇,好多骑手主动和我聊天,我也会带他们去北大转转、交流。我发现保持自己和他们的不同,反而能更容易进入他们的世界。如今,点外卖已经很普遍了,但大部分人不了解,一份外卖送到你手上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?你真的不会知道他为什么送得快,为什么送得慢?他送得快可能是因为闯了红灯,送得慢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交警或者出了车祸。我们都无法阻挡技术的发展,我们人类能做的,一个是在制度上进行一些调整,不要让技术成为人的枷锁。比如社会保障、基本的劳动保障,现在骑手群体都是没有的。如今,平台经济又被称为“零工经济”,不仅是外卖骑手,凡是经由平台经济兴起的职业比如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等,都是散工。他们的工作时间灵活,工资按件提成,但没有社保,也不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。但系统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困局的。
另一个可以抵挡数字异化的方法,我觉得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、理解和包容,这也是我想写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表达。我一直相信,系统一定是会存在漏洞的,只是大小问题。算法和数字也一定有它的边界,它不会无限蔓延到人的每一个角落,而是存在它鞭长莫及的地方。比如一个久经沙场的骑手,在拿到订单的一瞬间,他就可以估摸出大概多长时间可以送到。这完全是凭借一种个人的经验和直觉计算出来的,而不是数据。这个时候,他就可以思考和抉择,我要不要再拿几个订单再出发?我要不要欺骗平台说还没送到?又比如让很多骑手头疼的“确认到店”。现实中,如果遇到商家出餐慢,骑手可以向平台报备,报备后可以多得到5分钟的等待出餐时间。但平台对是否到店的判断是通过距离测量,500米内就可以点“确认”了。而在一个店铺密集的商业街,熟练的骑手可以在距离餐厅500米以内但还没到店的时候先点确认,为自己争取时间。
还有送餐的时候如果来不及了,我们可能想要打电话给顾客说声对不起,然后询问能不能提前点送达?有次我打电话给一个女顾客解释,她很爽快地说没问题,你看着弄就行。那一刻我内心真的极其温暖,我太感激她了。因为一旦我点了确认送达,她就不能在手机上看到我了,她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送到。这里面有一种数据无法量化的信任。这些灵活的东西,是数字技术永远理解不了的。它永远也想不到,在点了“送达”之后,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交流和商定。不只是外卖骑手,在今天,数字控制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每个人身上,也会加剧人和人在现实中的疏离。但我觉得,越是在被数据全方位侵蚀的时候,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、交流和理解,越是凸显出重要性。这种情感的辨认和呼唤,反而能帮我们努力抵挡被数字的异化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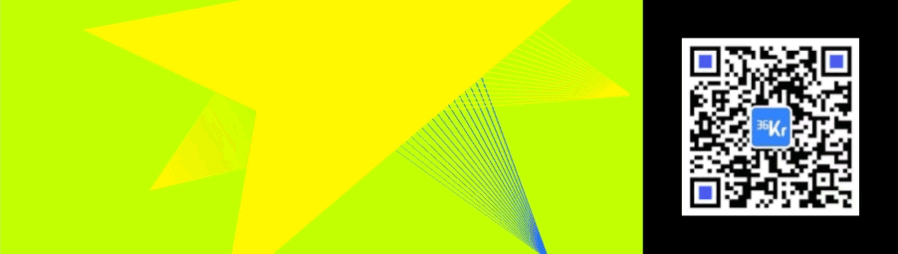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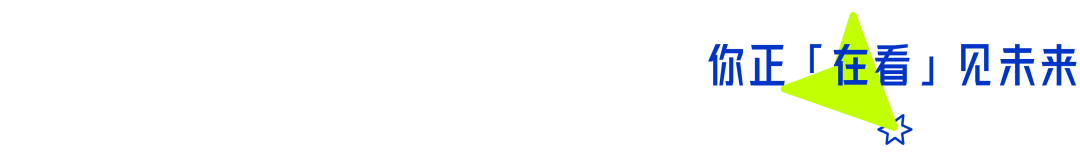
中关村这个团队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外卖骑手队伍之一,成立于2015年,如今已从十几人的小团队发展壮大到了八百余人的大团体。...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,保利特别不好意思,他觉得周围都是北大学生,他自己是个送外卖的,还穿着制服,怎么好意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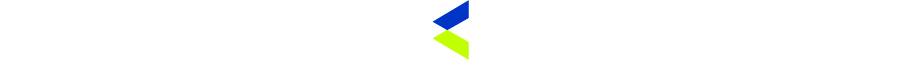
几年前,一条“北大博士后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”的新闻,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、博雅博士后陈龙跻身公共讨论视野。作为每天穿梭在城市里的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,外卖骑手构成了这个平台经济时代里最典型的零工样本。早在2018年,陈龙就开始了对外卖骑手群体的研究和体验。为了完成博士论文,他加入了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骑手站点,扎扎实实地跑了半年外卖。2024年底,他将自己亲身体验和研究的结果和16万字的采访资料,汇集在了新书《数字疾驰》里。
陈龙在前期调查时发现,仅单一平台的公布数据,就有约300万外卖员,“但这300多万人不是在一个实体的公司,而是分布在全国2000多座大大小小的城市里,每天走街串巷,看起来杂乱无章,但都能准时准点地把外卖送到你手里。”陈龙好奇,这背后的主导秩序究竟是什么?本应赋予人更大灵活度的数据,如何编织成困住人的庞大网络?随着科技的进步,资本对劳动控制的强化、系统及其背后的“数字控制”,又如何构成了今天这种独特的劳动秩序?《数字疾驰》共分为三篇,从骑手团队的人员构成,到亲身上路跑单的亲身感受,从“人造单王”女骑手,到“挂单”“报备”等具体而微的平台漏洞,全书以“网”“线”和“点”的结构,将骑手与平台系统、商家、顾客、站点、保安甚至交警之间的复杂互动模式串联起来。《数字疾驰》以局内人视角,揭示数字控制之下新型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如今,书中详细呈现的几位受访者,大多都已经不再送外卖了。有的去南方进了工厂,有的做起了保险销售,有的回老家带孩子。结束研究后,陈龙又花了三年多时间进行样本搜集与采访。最终,他得出结论:随着科技进步与资本对劳动控制的强化,平台、系统及其背后的“数字控制”,构成了新的劳动秩序。也正是在切身体验过这一职业后,陈龙意识到,某种角度而言,系统的确可以困住骑手,但永远无法真正困住人,也无法参与真正属于人的灵活性与复杂性。以下是陈龙的讲述。
成为他们
2018年夏天,我还在念博三,住在北大的一座学生宿舍。每天下楼都会路过很多外卖骑手在门口等着学生下来取餐,但我天天见到他们,其实都有点熟视无睹。后来,是在我导师的建议下,我最终决定将这一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确定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。
确定下来后,我意识到自己首先得成为外卖骑手。而且成为一天两天、一两个月不够,我必须熟悉这个群体的工作模式。我到网上去投简历,用地址为山西老家的过期身份证,编了一堆假的经历,几经辗转,最终成功加入了位于中关村食宝街的一个站点兄弟连。站点的性质有点像平台的加盟商。外卖刚开始出现的时候,平台是直接雇佣骑手,但随着骑手数量越来越多,平台就不想雇佣了。因为雇佣的成本很高,要签劳动合同。于是,他们把骑手的招募和管理外包给劳务公司,加盟商们会把某一片区域的平台订单都承包下来,设几个站点,按站点招募骑手。中关村这个团队号称是中国最早的外卖骑手队伍之一,成立于2015年,如今已从十几人的小团队发展壮大到了八百余人的大团体。我刚加入的时候,当时的站长说过一句话:“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。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,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。”不过,送外卖第一天,我只送了9单。那时候比现在贵,一单能赚8块,一天下来,我赚了72块钱。刚开始我跑得比较节制,下午三点收工后就去找骑手做访谈,跑得也不太专心,满脑子想着我的调查。我仍然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的。但随着研究进展阻滞不前,我越来越焦虑。这种焦虑大概持续一个月后,我意识到,不行,必须先放下研究这件事儿,全心全意地投入跑外卖。我所在的中关村兄弟连,毫不夸张地说,简直是“藏龙卧虎”。什么样的人都有,有创业失败的、身负债务的中年人,也有去年那部电影《逆行人生》里徐峥饰演的曾经的中产。
对他们来说,送外卖是一项可以立刻来钱的工作,不需要高学历、技术门槛,一辆电瓶车,一台手机就行。在北京,如果非常努力地跑,一个月还是能拿到1-1.5万,这对很多三四十岁忽然失去工作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。这几年一直有传言,说外卖员的平均学历越来越高。最开始是某平台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,经统计,外卖骑手群体里本科以上学历者高达20万人,研究生学历甚至达到7万,高学历外卖骑手占比20%多。但其实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。因为它面向的是平台注册的所有骑手,可不意味着所有骑手都会填问卷。比如有好几百万骑手,最后好像只收回来了6万份问卷。我接触的骑手们,大部分还是来自小地方的、低学历的。他们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来务工人员,来送外卖往往是因为身上背负着经济压力。据我观察,经济压力最大的骑手大致分为三类:第一个是有养家重任的青壮年男骑手,他们是最能“拼命”的一群人;其次是单亲妈妈;最后是已婚已育的女骑手——可能老公在其他地方打工,家里还有一两个孩子。我从2018年3月开始跑外卖,直到8月底,经历了北京的早春到盛夏。天气对跑外卖的影响很大。某种程度来说,外卖骑手和他们的父辈一样,尽管远离了黄土地,但本质也是“靠天吃饭”的行业。但不一样的是,对骑手来说,反而是越恶劣的天气,越有钱赚。夏天顶着烈日走街串巷,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有多热,而是我经常穿的那件绿色T恤,一个夏天过去,竟然全部被汗水浸褪成白色了。当时我有个站点里认识的朋友,他租住在城中村自建房里。有一天,他给电瓶车充电的时候,电瓶车忽然着火了。他第一时间担心的是把人家房子给烧了,情急之下竟然直接徒手抓着电瓶就往外搬,火就一直顺着他的胳膊往上烧。前几天我和那位朋友还一起吃饭,七年过去,我还是看见他的整只手臂几乎都是乳白色的疤痕。北京的冬天比夏天更难熬。我刚开始跑的时候还有倒春寒,有时会下雪。但捂得太严实也不行,因为跑着跑着会出汗,然后就变成了外面冷风嗖嗖地吹,衣服里面却已经被汗水湿透了,我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把汗烘干。雨衣根本不管用。雨水钻进衣服里,同样只能靠体温硬生生把水分蒸干。我至少还可以回宿舍洗热水澡,但很多骑手为了省钱,都会住在没有卫生间的城中村房子里。我在书里提到的来自甘肃的保利、春生,来北京后两个月没洗过澡。我带他们去北大的学生澡堂洗过一次澡。我记得很清楚,当时,保利特别不好意思,他觉得周围都是北大学生,他自己是个送外卖的,还穿着制服,怎么好意思?我告诉他,在澡堂里,大家都没穿衣服,脱光后就会发现,我们都一样。
另一种控制
大概跑到第三个月,我想要研究的问题终于开始渐渐明朗:我所在的那个平台号称全国有三百万外卖骑手,这三百多万骑手同时分布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,但我好奇,到底是谁在指挥这三百万外卖骑手?如此大体量的劳动者,他们看似有条不紊的这种生态和规则,究竟是如何形成的?与工业化生产时代相比,互联网平台劳动者似乎拥有很大的“自由”和“自主性”。所以今天我们常听到说,很多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,但不愿去工厂。在一定程度上,送外卖的确是更“自由”的。但这份自由是相对的,很多骑手口中的自由,指的是他可以在工作中“手脑并用”。他既需要不停奔波,也需要不停地动脑,一边看路线,一边和商家、顾客甚至是交警互动。相比起封闭的流水线工厂,外卖骑手其实算是一份具有社会性的工作,至少不用将自己变成劳动的机器。
在这个意义上,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。而在赚钱差不多的情况下,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更倾向于选择更有自由的工作。但这种相对的自由之上,还是悬挂着更精细的数据控制。从取餐那一刻开始,骑手就要开始一路的“打怪”送餐之旅。路途中不可预料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红绿灯、交警、交通意外。在繁忙的中关村商圈,红绿灯对骑手来说只是摆设,几乎没有骑手会真的停下来等红灯。团队里的一个骑手顾少聪直接告诉我:你不闯红灯,就挡了后面要闯红灯的骑手的路。骑手的工作时间大多是从上午9点到晚上9点,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高峰期,订单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段。在这期间,由于订单量激增,平台系统会进入疯狂派单状态,骑手接收起订单来也会应接不暇。一般来说,一位骑手完成一起订单的时间在25~50分钟之间,但由于高峰期系统不停地派单,每位骑手手里都积压了大量订单。而在订单时间重叠效应的影响下,每单的送餐时间会被成倍压缩。于是,一个矛盾困境诞生了:送餐时间越短,超时的概率反而越大。最理想的效率,是通过复杂的数据计算,让自己恰好置于一个两方都平衡的时间点。
在众多的“线”中,外卖骑手与平台系统之间的互动是占据主导地位的。整个劳动秩序维系的关键就在骑手服从平台系统的指挥,而平台系统不断地收集骑手、商家与顾客的数据,并将数据分析的结果用于优化骑手匹配、线路规划、时间预计、配送定价等维系劳动秩序的方方面面。在骑手工作的时候,平台会不断收集他们的所有数据,并且通过对这个数据的分析反过来优化对骑手的管理。比如,一个骑手可能在送外卖的时候发现哪个地方有一条近路,可以帮他节约时间,这个时候系统就会优化,发现你明明可以20分钟送到那里,于是就不再会给你45分钟的时间。一般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,骑手在外面奔波、抢时间,很苦很累,但我在亲身体会后发现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。刚开始可能的确觉得辛苦,但跑了一段时间以后,其实你根本不在意有多累,你在意的是系统如何给我派更多订单,让我在更短时间内赚更多钱。你就是会不由自主地想,我昨天跑8个小时,明天一定要跑10个小时,后天要跑12个小时。我昨天只跑了20单,明天就要想办法跑30单。就像我在书中提出来的,骑手是一个不断探索人的劳动极限的工作。你做这份工作的时间越长,系统其实越会扩展你的极限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,就有美国科学家提出了“数值控制(numerical control)”的概念,那时候主要是讲计算机,通过数值来操控机器或是操控人。而我们今天说的“数字控制”特指平台经济时代数字对人的控制。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,平台经济的核心是系统,而系统的核心,是数据。总的来说,平台系统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管理效率的极大提升,将劳动秩序纳入可计算的程度,实现了对劳动的高度控制和精准预测。这种控制看起来很可怕,像是现代的另一种对劳动的异化。可我想,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空间和缝隙,可以容纳人的独特可能性。
数字的盲区
2021年,一条“博士生送外卖”的新闻将我送上了热搜,接受过一次采访后,铺天盖地的媒体打电话来找我。那时候,其实我很惶恐。因为新闻报道会突出我,“博士生送外卖”的这种对比会变成噱头。直到现在,一些人在介绍我的时候还是会说,陈龙是当年那个去送外卖的博士生,这很了不起。虽然是在赞誉我,但本质上就是将我作为关注主体。而我研究的和希望呈现的外卖员却隐身了。就在昨天(采访前一天),我还和当年认识的几个外卖员朋友吃了顿饭。一共六个人,只有一个是我在2018年就认识,而且至今还在送外卖的。剩下的大多都已离开外卖行业,有两个人在卖保险,书中的其中一个主人公保利如今在浙江一个工厂里。而大家离开的原因,无外乎“太苦、太累、风险太大”。
在我体验的那半年里,刚开始我也很犹豫,到底要不要把我做研究的本意告诉大家?一方面,我担心研究者的身份会让他们产生距离感。但另一方面,我也希望自己能坦诚与他们相处,不必担心问东问西而显得可疑。直到研究快结束的时候,我才开始告诉一部分亲近的骑手,再有人来问我之前在做什么的时候,我就直说自己是个学生,放暑假想出来挣点零花钱。这么说了以后,他们反而对我产生了更多好奇,好多骑手主动和我聊天,我也会带他们去北大转转、交流。我发现保持自己和他们的不同,反而能更容易进入他们的世界。如今,点外卖已经很普遍了,但大部分人不了解,一份外卖送到你手上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?你真的不会知道他为什么送得快,为什么送得慢?他送得快可能是因为闯了红灯,送得慢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交警或者出了车祸。我们都无法阻挡技术的发展,我们人类能做的,一个是在制度上进行一些调整,不要让技术成为人的枷锁。比如社会保障、基本的劳动保障,现在骑手群体都是没有的。如今,平台经济又被称为“零工经济”,不仅是外卖骑手,凡是经由平台经济兴起的职业比如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等,都是散工。他们的工作时间灵活,工资按件提成,但没有社保,也不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。但系统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个困局的。
另一个可以抵挡数字异化的方法,我觉得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、理解和包容,这也是我想写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表达。我一直相信,系统一定是会存在漏洞的,只是大小问题。算法和数字也一定有它的边界,它不会无限蔓延到人的每一个角落,而是存在它鞭长莫及的地方。比如一个久经沙场的骑手,在拿到订单的一瞬间,他就可以估摸出大概多长时间可以送到。这完全是凭借一种个人的经验和直觉计算出来的,而不是数据。这个时候,他就可以思考和抉择,我要不要再拿几个订单再出发?我要不要欺骗平台说还没送到?又比如让很多骑手头疼的“确认到店”。现实中,如果遇到商家出餐慢,骑手可以向平台报备,报备后可以多得到5分钟的等待出餐时间。但平台对是否到店的判断是通过距离测量,500米内就可以点“确认”了。而在一个店铺密集的商业街,熟练的骑手可以在距离餐厅500米以内但还没到店的时候先点确认,为自己争取时间。
还有送餐的时候如果来不及了,我们可能想要打电话给顾客说声对不起,然后询问能不能提前点送达?有次我打电话给一个女顾客解释,她很爽快地说没问题,你看着弄就行。那一刻我内心真的极其温暖,我太感激她了。因为一旦我点了确认送达,她就不能在手机上看到我了,她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送到。这里面有一种数据无法量化的信任。这些灵活的东西,是数字技术永远理解不了的。它永远也想不到,在点了“送达”之后,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交流和商定。不只是外卖骑手,在今天,数字控制发生在现代社会的每个人身上,也会加剧人和人在现实中的疏离。但我觉得,越是在被数据全方位侵蚀的时候,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、交流和理解,越是凸显出重要性。这种情感的辨认和呼唤,反而能帮我们努力抵挡被数字的异化。